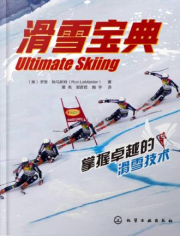 【书 名】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
【书 名】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
【作 者】(美)凯尔·哈珀 著 李一帆 译
【出版者】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索书号】K126/6816
【阅览室】社科二阅览室
作者简介
凯尔·哈珀是俄克拉何马大学古典文学和文学教授、资深副校长兼教务长。哈珀在俄克拉何马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哈珀的研究集中在横跨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早期的社会和经济史上。哈珀的作品还有《晚期罗马世界的奴隶制,公元275—42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年)。这本书被美国历史协会授予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奖,并被中西部和南部古典协会授予杰出出版奖。
李一帆,2012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数学系,数学与统计专业学士与硕士,业余从事考古及相关资讯翻译。
内容简介
本书论述的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章节之一:罗马帝国的灭亡。《罗马的命运》是第一本研究气候变化和传染病在罗马帝国的崩溃中所起作用的著作,叙述了自然战胜人类野心的故事。
凯尔·哈珀将宏大的历史叙述与最为尖端的气候科学和基因研究结合在一起,指出罗马帝国的命运不仅是由皇帝、士兵和野蛮人决定的,也是由火山爆发、太阳周期、不稳定的气候以及致命的病毒和细菌决定的。他从罗马帝国的二世纪的巅峰时期一直叙述到七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支离破碎的局面。哈珀描述了罗马人在巨大的环境压力下如何复苏,又如何再次面临危机,直到再也无法承受“小冰河时代”和反复爆发的鼠疫的打击。
《罗马的命运》深刻地反映了人类与环境的密切关系,全面描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是如何面临和忍受环境的压力,最终依然崩溃的。罗马帝国的例子提醒我们,气候变化和细菌进化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塑造了我们居住的世界。
罗马的公民军团是一种义务兵役,拥有公民身份的罗马人自费购买武器装备,因此兵种通常由个人的财富来决定,例如富裕的公民通常为骑兵。人们视服兵役为一种荣誉,而不是生存手段。职业军队则由国家提供装备并提供薪水,雇用无产市民,或想通过军队晋升从而实现阶级跨越的年轻人,退伍后通常可以在殖民地得到一块土地安居,军人由此变为一种职业。—译者注。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或编者加,后面不再标出。
帝国治理方案。
通过将税收工作留给当地贵族,并且慷慨地授予这些人公民身份,罗马人把三大洲的精英揽入统治阶层,从而只靠几百名高级罗马官员,就管理了一个庞大的帝国。现在想来,帝国从单纯的索取机制变为一种利益共同体,所经历的时间之短暂,实在令人称奇。
帝国的持久性取决于这一“重大交易”(grand bargain)。这是一种策略,并且收效甚好。在“罗马治下的和平”时期(pax Romana),随着掠夺变为统治,帝国和其统治下的许多民族繁荣起来。最先增长的是人口,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人口成倍增长。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城市超出了其惯有的人口限度;定居地内的密度明显增加。森林变成新的农田,原有的农场延伸到山坡上。在罗马帝国的阳光下,似乎所有的有机物都在茁壮生长。大约在这个时代的第一个世纪里,罗马城的居民很可能超过了100 万。罗马是第一个达到这个数字的城市,并且在 1800 年左右的伦敦之前,是唯一达到这个数字的西方城市。在 2 世纪中叶的鼎盛时期,大约共有 7500 万人生活在罗马的统治下,占全球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
在生活节奏缓慢的社会里,这样的持续增长—以这种规 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很容易带来厄运。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非常有限。随着人口激增,人们被推向越来越贫瘠的土地,越来越艰难地从环境中汲取能量。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很了解人类社会与其食物供应之间的内在和矛盾关系。“人口增加的能力远远大于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的能力,因而人类必然会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过早地死亡。人类的各种罪恶积极而有力地起着减少人口的作用。它们是破坏大军的先锋,往往自行完成这种可怕的行为。如果它们在这消灭人口的战争中失败了,疾病流行季节、时疫、传染病和黑死病就会以吓人的队形进击,杀死无数的人。如果仍不能完全成功,严重而不可避免的饥馑就会从背后潜步走近,以强有力的一击,使世界的人口与食物得到平衡。”
然而......罗马人显然没有毁灭于大规模饥荒。我们可以从这个事实中发现帝国成功的隐性逻辑。面对人口的飞速增长,罗马人非但没有陷入悲惨的境地,还实现了人均经济增长。帝国能够无视,或至少是推迟了“马尔萨斯压力”的残酷逻辑。
在现代世界,我们习惯于经济每年增长 2 至 3 个百分点,我们的希望和养老金都系于此。在古代,情况却并非如此。由于自身的性质,工业化前的经济在能源方面受到很大限制,在任何可持续的基础上更有效地提取和交换能源的能力受到局限。但是,前现代历史既不是一个缓慢地、稳步地通往现代化的过程,也不是俗话所说的曲棍球棒——直到工业革命非凡的能源突破之前,一直一成不变地维持在生存水平线上。事实上,它的特点是脉冲似的扩张和解体。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提出了“全盛期”(efflorescence)的说法,用于形容一些扩张阶段,这些扩张阶段的背景条件有利于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实现真实的增长。随着人口成倍增加,并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生产,这种增长是粗放型的,但是正如马尔萨斯所说,这种增长的空间最终会耗尽;更有希望的是,当贸易和技术使从环境中获取能源变得更有效率时,可以实行集约型增长。
罗马帝国为一段有历史意义的“ 全盛期”奠定了基础。早在共和时代晚期,意大利在社会发展方面就已经经历了超前的飞跃。
在某种程度上,意大利的繁荣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单纯掠夺的结果,是作为征服成果的政治租金。但是,在掠夺而来的财富外表之下,真正的增长正在进行。这种增长不仅在武力扩张达到极限之后继续,并且开始在所有被征服的土地上散播。罗马人不只是统治领土,将外围地区生产的盈余运送到帝国中心。实际上,帝国的结合是一种催化反应。罗马的统治缓慢而稳定地改变了其治下社会的面貌。商业、市场、技术、城市化:帝国及其境内许多民族都抓住了发展的杠杆。在 150 多年的时间里,在广阔的地理范围内帝国显然同时实现了集约型和粗放型的增长。罗马帝国既延缓了马尔萨斯的审判,又赢得了极大的政治资本。
这种繁荣是帝国辉煌成就的前提,也是其结果,这是一种迷人的循环。帝国的稳定是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有利背景;人民和繁荣反过来又是帝国权力的有效保障。国家兵源充足,税率虽然不高,但收税对象足够丰富。皇帝们慷慨大方。帝国与城市精英阶层达成的重大交易成就了双赢的局面。似乎到处都有足够的财富。驻守边界的罗马军队在战术、战略和后勤方面都优于敌人。罗马人达到了一种有利的平衡,尽管比他们想象中的或许更脆弱一些。吉本伟大的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就是从描写 2 世纪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的。引用他著名的见解:“如果要一个人指出在世界历史的哪一段光阴中,人类的生存状况最幸福最繁荣,他会毫不犹豫地说,是从图密善去世(96 年)到康茂德即位(180 年) 之间的这段时间。”
罗马人向外拓展了一个前现代社会在有机条件下所能到达的极限。如此庞然大物的陨落( 被吉本称为“ 这场可怕的革命”) 能够成为人们一直痴迷的对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变幻无常的星球
到了 650 年,罗马帝国已经不过是昔日的影子,只剩下由君士坦丁堡、安纳托利亚,还有地中海另一边零星散落的领地组成的残存的拜占庭国家。西欧被分裂成许多好斗的日耳曼王国。前帝国的一半领土被来自阿拉伯的信士军队迅速占领。地中海世界曾经拥有 7500 万的人口,现在可能稳定在这个数字的一半左右。罗马城只剩下约 2 万居民,但他们却没有因此变得更富有。7 世纪时,一条不太起作用的主干航线仍然连接着东部和西部地中海。货币体系如同中世纪早期的政治马赛克一样支离破碎。所有金融机构都消失了,只剩下最原始的那些。无论在基督教世界,还是正在形成的伊斯兰世界,都弥漫着对末日的恐惧。世界末日就要临近了。
这段时期在过去被称为黑暗时代。我们最好把这个标签放在一边。它让人不可救药地回想起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偏见,并且,它完全低估了被称为“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活力和不朽的精神遗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必委婉地表述帝国解体、经济崩溃和社会简化的现实。这些都是需要解释的残酷事实,就像电费单一样客观存在,并且也用类似的单位来衡量。从物质方面来说,罗马帝国的衰落是“全盛期”的一种反过程,人们获取和交换能源的能力越来越弱。我们所凝视的是国家衰败和停滞的重要一幕。在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经过不懈努力创造出的一种衡量社会发展的通用准则中,罗马帝国的衰落被看作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