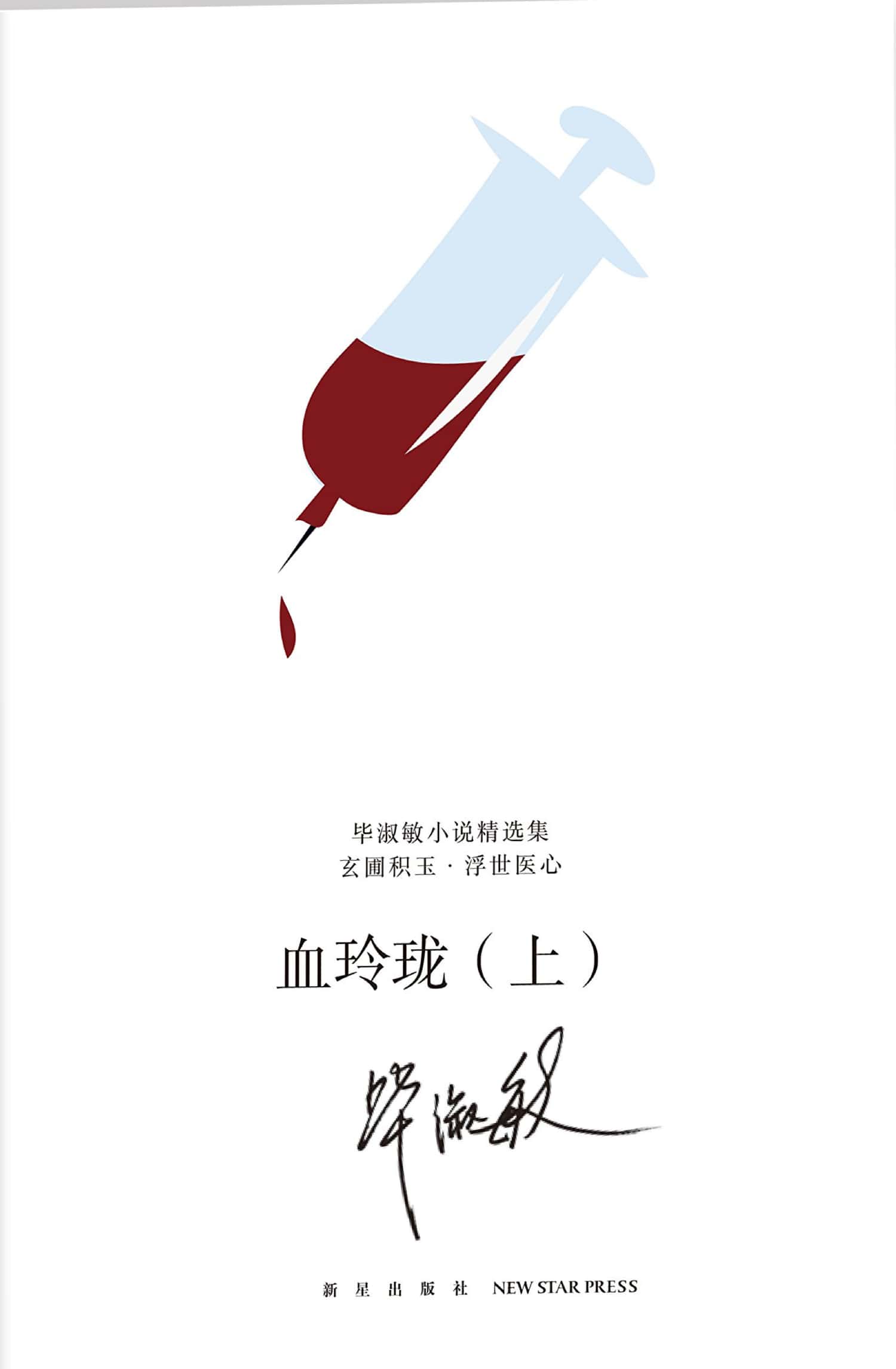
【书 名】血玲珑
【作 者】毕淑敏 著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索书号】I247.5/2238(4)
【阅览室】社科一阅览室
作者简介
毕淑敏,女,汉族,1952年出生于新疆,祖籍山东文登。1969年入伍,在西藏阿里当兵11年;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1987年发表处女作《昆仑殇》,198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共发表作品200余万字。作品曾获各种文学奖30余次,多篇文章被选入现行新课标中、小学课本。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心理学家。
内容简介
《血玲珑(上下)》是一部主题为“心灵救赎”的小说,更深层次的探讨“存在”与“生活”的意义。毕淑敏既是医生,又是作家,她以女性的细腻和敏感来挖掘女性的内心世界,用手术刀一般的文笔来揭示母爱、思考生命、审视女性自身所走过的道路。文字质朴简单却有风骨、有主张,洞明练达,舒爽清晰,带给读者最舒适的阅读体验。
序言
文字在我们的脑海中驻扎,必有一个固定地址。距离它最近的邻居,是这个人的灵魂之塔。
每个字是—块砖,几百万字垒起来,就是一个小院了。给自己的作品作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拖了很久。我不喜欢向后看,但这—次,必须回头,绕着院子走一圈。
多年前曾参加过一堂外籍心理学家的专业课。开课伊始,老师二话没说,拿出了一个亮闪闪的金属球。他手掌向下,把球放开,那球就垂直地停在他手指下方约—尺的地方。座位较远,我看不到更多的细节。按常识推断,我猜他手指中捏着—根细线,线的下揣拴在金属球上。也就是说,这个金属球像一个沉重的钟摆。果然,片刻之后,他用另外一只手从某个方向强力推动了那颗球,球快速摆动起来。当晃到某个特定的角度。我果然看到了—根线。
不知道剖币卖的是什么药,同学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和那个球。老师笔直地站立着,手掌向下,肃然不动。金属球不停地荡着,摆幅渐渐缩窄。这个过程在凝视中显得很长,满堂死寂。终于亮闪闪的球困乏了,震颤着抖了几下,寿终正寝似的停住。
你们从这个过程中,看到了什么?老师发问。
学生们开始作答。有人说,这证明永动机是不可能的。有人说,他在此过程中看到了力量。有人说,他看到了改变。还有人说,牛顿的苹果万有引力。更有人说第一推动力是上帝之手……
老师频频点头,好像每一个回答都正确。但我看出来那只是习惯动作,他扫视全场。焦灼地问,还有新的发现吗?无人回应。前述每一个回答都精彩,再无更惊艳的说法。
心哩学家有些是很古怪的。此人基本上算一个。我不喜欢这种脑筋急转弯式的问题,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然心态,静观其变。傻看了半天,老师还是毫不回转地等待。我很希望这个环节赶紧跳过去,突然就举了手。我被自己吓了一跳,胳膊居然不听大脑差遣,成了篡位的叛国将领。
充满失落和执著的老师,看到有人终于响应,急切道:你!看到了什么?
天啊,直到这一刻,我还没想出来该说什么。不过,我必须说点儿什么,要不简直就是滋扰课堂。我战战兢兢道,我没有别的意见,就是希望您快讲正式的课。
老师倨傲地说,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你刚才究竟看到了什么。如果你实在没有新的看法,把别人的回答再说一遍也可以。之后,你会听到我的授课。
我匆忙判断了—下形势,明白不管我答得如何错乱,老师准备就坡下驴了。我愿意成全,又不想重复他人,慌不择路地说——我看到了时间。
老师眉梢乱抖,夸张地显示他的大喜过望,说:哦!好极了!时间本来是隐形的,但你现在可以看到它现身,从不动到动,从动到不动。我开讲心理如何始终处于时间流变中……
那天的课程究舒井了什么,已然忘却。唯有金属球还在记忆中沉甸甸坠摇。
我发表处女作时已经35周岁了,一个老态龙钟的开端。那篇小说叫做《昆仑殇》,主题是尊严与生命,还有人的精神不屈。多年以来,我—直秉承着这个方向,迄今为止,并无改变。我是一个医生出身的写作者,从医二十多年的经历和训练,让我始终无法跳脱出从医生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我无法评说这个角度是好还是不好,但我知道沉淀在血液中的一些东西,难以过滤。
我刚开始写作就从中篇小说人手,不合常理。原因很简单,壅塞在喉咙里的话太多,篇幅短了说不完。而且我也不知道中篇和短篇小说有什么重要分别,以为只是长短的不同,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既然话多,就一个劲儿写下去,直到胸中的那一口饱含雪山冰冷的长气出完,这才告一段落。1987年,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才晓得了自己的冒失,违背了先短后长的惯例,冲撞了文学规律。于是自惭形秽,赶紧调回头来学着写短篇。在这个时间段内,中短篇小说创作量比较多一些。1994年,我的短篇小说《翻浆》和极短篇小说《紫色人形》'在台湾获得“第16届中国时报奖”和“第17届联合报文学奖”。获奖算不得什么大事儿,但我自忖这个缺漏补得大致说得过去了,从此可以率性去写长—点儿的东西。我开始写长篇小说《红处方》,费时一年多,1997年出版。之后我大约几年时间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有了2001年的《血玲珑》,2003年的《心理小组》,2007年的《女心理师》,2012年的《花冠病毒))。长篇小说的工作周期比较长,精神和体能的弦不能永远绷得铁紧。需要加以分割。加之长篇小说从刨作到取得一笔稿费的间隔比较长,好几年才能有—次收成,且不固定。为了抒发心中不时涌出的万千感慨,也为了得些小钱补贴家用,我在长篇小说的间歇节奏中,会写一些散文。多年积攒起来,大约也有了几百篇。这期间也曾写一些中短篇小说,数量不多。概因写作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劲道不一样,如同舞动长枪和短匕。技巧有分别。我很抱歉自己是个不能一心二用的人,只好基本放弃中短篇小说的写作。散文则似乎和小说创作有轻度的绝缘,可从心所欲、互不相扰。
按时间顺序捋了一遍我的创作,自己也有豁然开朗之感。原来是这样啊!时间真是值得尊敬的单向街,它是组成我们生命的最原始的材料,一切都埋藏其中。
一个人说儿点谎话不难,但要连续在几百万字中说谎话,很难。所以,还是在文字中说真诚而且自己坚信的话吧,直抒胸臆,坦率待人,比较容易和快乐。我的小说,说穿了主题很简单。始终围绕着生命宝贵、人间冷暖、身心健康在喋喋不休地做文章,怕也是本性难移了。谁让我做过20年的医生,当过心哩咨询师,又是一个做女儿、做妻子、做母亲的平凡女子?我守卫过祖国最高的领土,看到过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峰峦。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我期望从自己的笔端,滴下带有冰碴的温情。我不深究自己的能力,只是坚持单纯的信念。尽力而为。
生命是死亡到来之前的有趣过程,我喜欢文字给予我的淡而绵长的幸福。我的写作,犹如那粒动荡的钢球,已经晃动了几十年。推动它的外力,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珍爱和渴望分享的激情。当我把对这个世界的话说完,会渐渐停下来,回归凝然不动的安息。
非常感谢简以宁女士的创意,出版我的小说编年体集,心中满溢感动。她不辞劳苦地把我多年前写的小说,从时间之水中打捞出来,像渔民晾晒鱼干一般陈列海滩。以备今日的读者们赐教。编年体小说集的好处,是让人们看到一个作者在流动的时间中的变与不变。
毕淑敏
写于2012年5月1日
文摘
命运经常以消息出现。
“卜总!”
女秘书姜娅闯进总经理办公室,飘起的一缕长发被夹进门缝。
卜绣文正在批往来的业务文件,头也不抬地说:“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我刚上班的第一个小时内,任何人都不见,任何电话都不听。”她沉下略显出眼袋的脸。
她要用最清醒的时间考虑最重要的事情,不得打扰。特别是今天,和商务对手匡宗元有一场艰巨的谈判,如同歌手的重要演出,她不愿被任何其他事物分心。虽然姜娅平时很得宠,卜绣文的音调还是带出斥责。但总的来说,气色还算平和,她不想一上班就批评下属,把自己的心情搞糟。对于一个举手投足都牵涉到决策和金钱的人来说,心情就是生产力,是财富的基本支点之一。
“早早病了!”姜娅并没被上司的脸色吓住,急急说道。她确知,在女老板心中,她的独生女儿夏早早,重于千笔生意。
没想到卜绣文面如秋水。她心里有数,上学的时候,孩子还好好的,分手才一会儿,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如果是出了车祸,那另当别论。但姜娅是训练有素的秘书,即使在慌乱中,她也说得很清楚:是病了,而非其他。
卜绣文镇静地问:“什么病?不会有什么大病的。”
“晕倒。学校刚来的电话,说是冷不丁就晕倒了,不知为什么。早早现正在回春医院抢救,医院要亲属快去。”
卜绣文依旧闲闲地说:“我马上要处理一笔重要业务,同匡宗元打交道,失约就先棋输一着。找早早爸爸吧,他的时间比我宽松。”
姜娅悄无声息地退下,不一会儿又闪身进来了。
“卜总,夏教授此刻正在课堂上……”姜娅很为难。“挣钱不多,时间还铆得这样死……”卜绣文长叹一声,按说关于自己家人的牢骚,是不该显露在外人面前,但卜绣文奉行在“小圈子的范围内,可以说真话”的政策。如果不管大事小事都要盘算一番,虚虚实实难免太累。所以,有时候,她口无遮拦,不像一个运筹帷幄的老板。
“那好吧,我去。姜娅,你想一个稳妥的借口,与匡宗元延期。”卜绣文说着,在文件上签了一个花式繁复的名字,站起身来。
她把略带僵硬的藏蓝色套装换下,穿上一身轻松舒适的便装,匆匆出门。
姜娅在卜绣文的身后凝目注视着,半是钦佩半是发愁。钦佩的是老板知道孩子病了,非但不惊慌失措,居然还记得换衣服,难怪她的生意做得这样兴隆,大事小事都胸有成竹。发愁的是怎样对匡宗元解释。本来,编瞎话让对方同意改变计划,是一个好秘书的基本功。但这个匡宗元生性多疑,谎话怎么说得既不伤他自尊,又给今后的会谈留下和缓的氛围,还真需费一点心思。
早早今天是去参加学校的演出,童声小合唱。那是几首词和曲子都很做作的歌,最近一段时间,由于早早总在家里练习,卜绣文也差不多能哼出来了。每天放学之后,早早也还要在学校练一段,休息的时间就格外少。孩子们不在乎唱的到底是什么,他们喜欢那种聚在一起,放声鼓噪的自由。犹如一群小青蛙,在湿热的池塘里,对着天空呼出闷气。
校方的电话说,演出时唱到一半的时候,夏早早突然在场上晕倒了,幸亏台上铺着地毯,孩子们又靠得很紧密,这才没有跌得鼻青脸肿。学校赶紧把孩子送往医院,一边火速同家长联系。如今各家都是一个孩子,担不起责任啊!
卜绣文确信已走出自己公司职员的眼光范围之外,神经和全身的肌肉就一下子揪紧了。一路紧赶,进了回春医院,扯住她看到的第一个护士,忙不迭地问:“我女儿在哪儿?早早在哪儿?”
胖墩墩的护士很生气,她胳膊上的软肉,隔着白衣被这个精干的女人捏得发痛。皮肤的不适和胖女人对瘦女人天生的嫉妒,使她恼怒:“谁知道早早是谁?什么时候来的?医院里的病人多了,你以为我是什么?计算机吗?克格勃吗?”
卜绣文发现自己的失态,调整了一下紧迫的眼神,讨好地说:“夏早早,我女儿……我急坏了,对不起……说是晕倒了,刚才打电话叫我们来人的……”
“噢,那边。三号。”胖护士揉着自己的胳膊,不耐烦地甩开她。
卜绣文凶狠地冲撞着,在人流中为自己劈开一条道路,全然没有了平日的淑女风范。
看到急救室明晃晃的红字,卜绣文顾不得墙壁上巨大的“静”字,猛烈打门。门没有她想象的那样沉重,很轻盈地旋开了,她几乎扑到地上。
屋内由于玻璃和不锈钢的器皿太多,处处反射着刺目和不真实的眩光。在一张高而洁白的铁床上,躺着她小小的女儿。夏早早轻松地微笑着,正在同身旁的护士说着什么,看到妈妈气喘吁吁地冲进来,不由得吓了一跳,大声说:“妈,您怎么啦?出了什么事,把您急成这个样子?”
